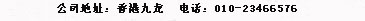冠心病病友和心内科医生的聊天秘诀
(一)
很早就想写这么一篇东西了,一直在等一个机会,哪成想这一等就等了十多年。
我是有一些“得天独厚”的条件的。首先自己是个心脏科医生,而且是个冠脉介入医生。而父亲,10多年前,就成了我的心脏病病人;更在大半年前,父亲又成了我作为冠脉介入医生以来一次植入支架最多的病人!
因着这样的渊源,也许在旁人看来,作为病人的父亲和作为医生的儿子之间,应该有许多次对话,或者是聊天。
既是父子,又是医患,这样的对话,一定是开诚布公,一定是无话不谈,一定是知无不言,一定是言无不尽......,总之,这样的对话,应该意义非凡,倘能广而告之,想来会给别的病友提供某种借鉴。
我一直没有等到,父亲也一直没给我这样的机会。
父亲是个识字的农民。一句话,我们父子医患之间不存在交流沟通的“技术性难题”。
仔细想,拼命想,10多年来,父亲确乎并未就自己的心脏病问题主动与我聊过天,哪怕一次也好。如果说我们之间有对话的话,也都是我在下“医嘱”,他在执行“医嘱”。
在父亲那里,没有“是否需要?如何做好?怎样管好?”的灵魂三问。
不错,父亲是在执着地践行着一件事儿:把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人干。他从开始就认准了儿子作为心脏科医生还是专业的,他很乐意自己不要多操心。
得到作为心脏病病人父亲毫无保留的信任和托付,不可否认,我是小确幸着暗暗欢喜的。
然而,这还不是我所认为的医患之间信任的最高境界。因为,我一直无法确定,作为父亲的他是信任儿子多一点,还是作为病人的他信任医生多一点儿。
(二)
现在,我已经不再那么期待与父亲进行医患之间的聊天对话了。而且,这样的对话,因为掺杂了亲情,似乎也不会成为纯粹的医患沟通对话的良好范本。
但我,一直期待着和我的每一位冠心病病友之间的聊天、对话和沟通。
我的那个“是否需要?如何做好?怎样管好?”的灵魂三问,并不是多么深奥的问题,也不仅仅是医生回答好了就可以的问题。
当素不相识的冠心病病友问我:我是否需要吃这个药?我是否需要做这个检查?我是否需要放这个支架?......
我不认为您的这些问题是对我们作为医生是否专业的质疑和怀疑。您的困惑和问题恰恰是我们彼此信任的开始,是我们可以头头是道地向您展示我们专业的时机。
因为这些问题,是我们医患都要认真对待和必须回答好的问题。
前几天,外地的一个冠心病病友,急性冠脉综合征发病,严重的冠脉三支病变(前降支完全闭塞,右冠的PDA和回旋支重度狭窄),心脏超声提示射血分数严重降低,不到40%了,心尖部室壁瘤形成且有附壁血栓。医院做了造影,可能因为病人很年轻且第一时间拒绝支架的关系,医院没有随即进行血运重建手术。医院,先看心内科医生,心内科又转给心脏外科,心脏外科说要搭4-5根桥,但要排队数月之后......。
小伙子的妈妈数年前从河北来上海,我给做的支架。他托了和我有联系的亲戚问我:自己应该怎么办?(是否需要?)
医患之间,这种通过中间人的聊天其实很不好玩。
因为有着前面病史的了解,加上看了冠脉造影的文字描述,我很明确地告诉他们:血运重建肯定是需要的。至于,冠脉搭桥好,还是冠脉介入好,因为当时没有看到造影结果,不好说。
之后,当我得知他从医院心内科,医院心内科,医院心外科,这样子兜了一圈子后......我最关心的,已经不是他什么时候到哪儿进行血运重建了!
这时,我们已经有了
转载请注明:http://www.damoson1980.com/gxbzlfa/7084.html